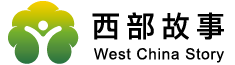我 家 就 在 河 边 住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黄羊镇广场中学 杨伟元
题记:一条河,她的名字叫石羊河。河的源头是祁连山的皑皑雪峰,千年冰雪融化汇聚成的河水,流经武威、金昌、张掖、白银等4市9区,绵延滋润着二百六十多公里的土地,最后流入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民勤红崖山水库。我家就在石羊河边住,从我家到河边有八百步,从河边到我家也有八百步。如果把石羊河比作母亲,那么我就是依偎在母亲怀中生活生长的孩子。
第一幕:听听那流水的声音
人们常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其实,石羊河何尝不是九曲十八弯呢,从皑皑的雪山之巅到曲曲折折的山间小溪,从涓涓的细流到静静流淌的林中小河,从汇聚着血液的心脏到渗入田间地头的丝丝血脉缕缕情怀,曲折蜿蜒,坚贞执著。没有喧哗,只有宁静;没有歌唱,只有低吟;没有索取,只有付出。石羊河,你虽然比不上黄河的波澜壮阔,但和黄河一样用自己的乳汁同样哺育着两岸的成千上万的代代儿女;你也有和黄河一样的臂弯把山石土沙花草树木飞鸟游鱼五谷六畜和自己的儿女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同在蓝天下,共饮一河水,在同一块黄土地上生活,繁衍。石羊河,你就是浓缩了的黄河,你就是黄河的一根动脉,即使在河上没有行船没有梢公没有水车没有羊皮筏子,但只要是母亲就会有同样的臂弯同样的情怀和同样的苦难。只是石羊河太小太浅,载不动千千万万生命中那一声沉重的叹息……。
皎皎凉州月,皑皑祁连雪。时间一旦逆着时空穿透历史的隧道,石羊河的水声就滔滔不绝了。这条河里,一些历史被吞没了,一些历史被重新冲起。看上去,它没有悲伤,没有忧虑,就那么流淌着该流淌的姿态,承载着该承载的负荷。在这条静静流淌的河流中,我踩着她过去的足迹,凝视着她现在的容颜,关注着她未来的面貌。一群儿女沿着河流冲刷的痕迹,步履蹒跚地走在它的河床上,我看到的是一棵棵春绿冬黄的白杨树分散地伫立在泥地里,沙土上,坚守着自己脚下的土地;我也看到了一丛丛红柳星星点点地装饰着黄沙的背景,根裸露着,叶凋落了,但红皮肤的本色依然没有改变;我还看到了一个个被砍去了树干留下的树桩,沉痛地心凝视着一道道伤疤,仔细品读树的沧桑,一圈圈年轮清晰可见,正诉说着岁月的变迁。躯体倒下了,但根还在泥土里;战士倒下了,但枪还握在手里;思想停止了,梦想还在延续。
我找不到曾经有过的那一大片的原始森林,我找到的是处处被风干后压弯了腰的一根根肋骨。石羊河是祁连山身上的一根肋骨,也是河岸上那些有灵魂的无灵魂的生灵们身上的一根肋骨。水少了,就成了沙;水没了,就成了漠。在石羊河瘦瘦的肋骨间,那些肌肉一样的嫩草也就枯萎了;草地枯了,人也就跟着萎了。我不知道它的过早萎缩,是否与它承载的战争的、文明的、经济的负荷太重有关?在历史的好多时点上,比如两汉、魏晋、前凉,比如唐朝,小小的石羊河在每个时点上,都曾经有过自己的繁华和昌盛。就如在唐代,这里是西北地区仅次于都城长安的繁华之地,因其“兵食恒足,战守多利”,被誉为“银武威”。在这块土地上萌生繁衍的龟兹古乐、西凉乐舞、狮子舞、攻鼓子舞曾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激起过多少多彩的浪花;五凉文化、佛教文化、西夏文化也曾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天梯山石窟、白塔寺、西夏碑、铜奔马等名胜古迹和文化遗存则更是镶嵌在华夏文明史上的灿烂明珠。就这样,一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地以它的盛世姿态承载过中原的灾难,拯救过中原的不幸,承袭过中原的文明,保存过中原的文化。在这期间,石羊河中不时流淌着看得见的战争的血和看不见的过度开发和掠夺的血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我时常觉得,石羊河有点像它养育出的凉州人,热情好客而又死要面子,家里的面柜里明明只剩一升面,也要全拿出来做一顿行面给客人吃;全家老小明明都饿着肚子,还要笑着说我的粮够吃;明明酒瓶儿空了,还硬要大碗喝酒,甚至在唱当地的歌时都要硬着脖子吼一声:“大碗喝酒不吃菜”——在一种豪爽中透着一些悲哀。
实际上,石羊河早已像一头老牛,喘息不止。河水两岸的子民,似乎知道这一点,但又似乎深通天意,因而他们谈起千年的负荷,没有一丝悔恨一丝抱怨。有的,就是不断地开垦,不断地扩地,不断地截水,不断地索取。于是,它的悲剧步着楼兰古城的后尘,先于黄河,先于东部的一条条小河而来了。沼泽,湖泊,泉水,森林消失了,河水两岸上,古道边塞里,总是弥漫着羌笛的哀怨,筚篥的呜咽,胡笳的悲鸣。绿洲消失、湖泊缩退、河流断道、耕地沙化等生态恶化的信号已经随着河水的日益减少而响起。在《乡土凉州》第96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93年5月5日下午,凉州区发生了特强沙尘暴灾害,平均风力7~8级,瞬间风力9~12级,能见度接近零。这次沙尘暴造成124人伤亡,其中死亡20人,重伤87人。全区31.6万亩经济作物受灾,11.05万亩粮食作物受灾,重灾面积达7.65万亩,3.1万亩果园正植花期,大部分花蕾被风吹落,减产4成以上;有16472棵树木被风刮倒吹折,引起火灾事故14起,烧毁房屋145间;有1200根广播杆倒伏或折断,断线11000米,;有280根高、低压高电线杆被刮倒吹折,变电设备被损;有114户乡镇企业因停电停产,减少产值308万元。在城区也因风灾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全区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843万元。
石羊河下游的西沙窝古绿洲就是警笛吹响狼烟升起的第一个地方。这里的地表组成物,以较疏松的河湖相粘土、亚粘土夹层的沙质沉积物为主,当一旦因水源不及或人为破坏大面积弃耕后,就会造成疏松地表直接裸露,在失去原有植被保护的情况下,风沙活动迅速加强,其生态环境潜在的不稳定性迅速激化,以致出现灌丛沙堆或形成片状流沙地,绿洲逐渐向荒漠演化,出现了大片流动沙丘。在靠近其东南部边缘毗近的现代绿洲处,则地下水状况稍好,绵延着一条宽约一公里的红柳灌丛沙堆带。西沙窝这种由东南向西北灌丛沙堆景观的逐渐变化,就是从唐朝开始的,它们也成了历史上绿洲沙漠化的主要标识。干旱地区自然生境严酷,雨量稀少,在天然状态下沙漠化土地的逆转很难,特别是因流沙侵入形成的沙漠化土地,沙丘流动,沙浪肆虐,自然的土壤粘化、生草过程极为困难,更无逆转的可能。西沙窝古绿洲自盛唐以后,千余年来的气候状况就从未有过多少改观。当元代以后重新向石羊河下游绿洲垦辟时,西沙窝古绿洲已经根本不堪复用,只能另择它处,在西沙窝的东侧另辟新绿洲,形成了现代民勤绿洲区。而今,绿洲在“搬家”,正在由下游移向中游。我仿佛看见了,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条绿龙在两条黄龙的左右夹击下节节后退,她正需要新的血液新的力量新的支持,才能打赢这场关于生死存亡的战役。
石羊河啊,你历史的负荷太沉了,太重了,有谁象你一样曾经拯救过中国历史的一段灾难,曾经支撑过汉唐历史的一页苍穹,曾经支撑过中华民族的一个辉煌时代?有谁能像你一样既具有战马长啸的战争画卷,又具有汹涌澎湃的诗情乐章?这样的历史,这样的重任,何以没有让如梦如幻的江南水乡、西子湖来承载?而让祁连山下一条战争硝烟连年不断的小河流水来担负?经年累月里,你总是隐蔽着自己的痛苦和惆怅,携带着大漠戈壁的雄旷,挟带着雪域高原的清冽,捎带着树林草原的苍莽,肩披着中原大地的凝重,踩着西部雄浑欢快的鼓点,从高山峡谷里搅动着汹涌澎湃的波涛,激荡着撼人心旌的漩涡。但谁能听懂,你那漩涡内长长不息的呻吟。
第二幕:正在消失的村庄
过不了多久,我眼前的村庄,可能就是湖区最后的村庄了。水没了,绿色没了,腾格里沙漠的连绵不绝的黄沙就成了村庄的唯一背景,而后被背景吞噬。村庄是一条河流的最后见证者,否则,一切将失去证据,历史仿佛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许多事情总是由于物证的丧失而被遗忘。所以我没有选择那些生态难民们走光了的村庄,作为证据记录,那些村庄已经成了无人的空壳,成了写在大地上的最后一个死亡的符号。
我选择的这个村庄,作为湖区的缩影,现在还有40多户人家,160多人,它正处在消亡的过程之中,在这里我更能看清它消失的轨迹和未来的走向。在这个村庄里,我同样找到了想要找到的老人。在民勤湖区都是一样,找老人容易找年轻人难。当一个村庄不能养育人时,年轻人是最先不恋村庄的人。老人那被风沙吹老的脸庞已经失去了表情,肌肉像萎缩、枯竭了的沙漠,失去了水份的滋润,目光呆滞的看着无云的天空。他叼着旱烟袋抽着呛人的漠河烟,黝黑发亮的烟杆上坠着一个树叶形的烟袋,绿色的,叶脉分明,经络清晰。他蹲坐在门台上,一个酒壶,一个酒盅,摆在面前,每隔一会儿,他会慢悠悠地,心不在焉地端起酒盅喝一口。那一刻,我听到了他在酒盅和干裂的嘴唇接触的一瞬间发出的“吱”的一声,仿佛那一声来自整个身体的中心,还带着心脏的微微颤抖。这里的老人喝酒不吃菜,也不喝茶水。我不知道是水比酒贵还是水比酒苦。想起曾经目睹了民勤人排着队用称分水的场面,我想,我已经体验到了老人喝酒不喝水的滋味。
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另一个小凳上。我能清楚地数出老人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但无法数清村庄之后的大沙漠上,风给沙漠吹出了多少皱纹。我无法数清老人脸上有多少根胡须,但能清楚地数出眼前沙漠上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有几棵梭梭,几棵红柳和几棵白杨。它们是一条河流最后的生命特征和生命所经历的最后的风雨年景。我已经看出来,老人想说许多话,但似乎又将所有想说的,放在了烈酒的倒影里。小小的酒杯,像一面镜子,收藏了老人经历的一切沧桑和烈性的激情。老人把酒杯推到了我的面前,要我也来一杯。我的眼睛在酒杯里摇晃,极想穿透这面镜子,遍览老人的从前。据说上帝造了水后造了人,人从一开始就围着水转,就被水的强力磁场笼罩;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就成了河床上一块块干枯死亡的石头。捡起一块千年的石头投放到河流奔流的时光里,在湖泊干枯、河水断流的时候,一条河流带走了太多的东西,生命里最美好的部分被日夜南侵的沙漠掳掠到另一个时空,剩下了沙漠里闪烁不定的沙粒本身。
老人和我走出街门,就看到了连绵起伏的沙丘,大漠上的热浪便扑面而来,烤得人的脸生痛生痛,嘴唇干裂,刺眼的阳光使我们的瞳孔无法适应,我们迷着眼,仿佛面对漫天风沙,辨不清天上地下东西南北。这里的房屋都是依柴湾而建,柴草死了,被沙压了,房屋,墙头,也就成了阻挡风沙的排头兵。但这对于大自然的淫威来说,作用微乎其微。房屋一经落成,就永不再长,而流沙却日日夜夜地在墙根里生长着个头。有时候,一场沙尘暴过后,房屋一夜间就被掩埋了。人就再让沙漠三分,往南搬一搬,再掩埋,再搬。这样动荡不安地不断搬迁,就是为了使自己的房屋与沙漠保持最近的距离,尽可能地阻止沙漠南移的速度。对于湖区的农民来说,抗击风沙与自己的生命等价。在民勤湖区,好多的家庭都已成了这样的结构,年轻人纷纷外逃、外迁,老人守留在故土。等年轻人在外创业有成了,有一个窝了,再把老人接出去。更多的老人则不愿出去,等待着让故土的风沙埋葬。翻开关于石羊河的书籍,我从白纸黑字间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记载:在历史的长河里,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许多湖泊,如著名的潴野泽、白亭海等,曾经湖面上碧波荡漾,青鸟游弋,湖边芦苇粗壮茂盛,近百种鸟类出没其中。这片绿洲的外围沙丘地上生长着沙枣、胡杨、红柳、梭梭等林木,在挡风固沙;这里还生长着干草锁阳麻黄等植被,宛如一片片绿色的地毯。这里的人们过着“上耕下渔”的生活。后来,湖泊逐渐变小干涸 ,绝大部分湖泊消失了,只保留着它们的名称,如邓马营湖、黑马湖、熊爪湖、武始泽等。干涸的湖地,现在大部分都被开垦为农田,有的已经被流沙埋没。如史家湖、陈家湖、李家湖、西湖、严家湖,这些村庄都是曾经存在的现在正在消失中的历史见证!
而更震撼我心灵的是绿色和树叶两个意象。老人为什么要把烟袋设计成一片树叶的形状?一片绿色的树叶,在沙漠中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人对村庄的从前、从前的从前的绿色和树木的回忆。现在,失去的岁月已经转化为信息凝聚于他设计的形象里了。一片树叶的每一根叶脉,都应该是湿润的,都应该携带着从树木根部传来的养分,汇集着大地的基因。它即使被风沙刮走,埋葬,仍然密藏着地上的根茎。一片树叶是一棵大树和一片森林的缩影,一片绿色是一块绿地和一片草原的见证。大树、森林和草原的全部力量、生命特征还有村庄已经被浓缩在小小的烟袋上了。这是它能够载负灵魂的秘密原因。烟袋仿制了这个秘密,它使用废弃的布料碎片用为原料,用绿色的线连接,里面装了烟草,又用一个能展示充分活力的外形来试图记载某段岁月的风景,这是一个隐藏了事物源头的烟袋。今天的孩子,除了满眼的黄沙,已经看不到那水,那绿色了,只能通过破译烟袋的秘密,才能想象他们从前和从前的从前的风光。
俯下身子,从黄沙地上拣起一片早已被风干了的树叶,丝丝叶脉间还在泛着绿色的光泽,上面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孔洞,就象天空里的星月一样。紧紧地捧住它,就象捧着一颗饱经沧桑的但仍然跳动着的心;轻轻地贴近耳边,仿佛在听了一位老人缓慢而沉重的诉说:“它在春风里绽出,阳光中长大。从冰雪消融到寒冷的秋末,它经受了虫咬石击,以致千疮百空,可它并没有凋零。它之所以享尽天年,完全是因为对阳光、泥土、雨露充满了热爱,对自己的生命充满了热爱。和爱相比,那些打击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三幕: 童年是一条河
快到“六一”儿童节了,我给七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一篇周记《童年,是____》。第二天,我翻开周记一看,记忆的大门便敞开了:童年,是一支歌,一首诗,一棵树,一个梦……。一个孩子就有一个童年的故事,一个故事就是一段生命的记忆。是谁的手轻轻拨动了记忆的弦?童年,我的童年是一条河,就是那条家乡的石羊河。河里溅起的朵朵浪花就是弦上跳跃的个个音符。
春寒刚褪,夏天一到,小草长到三四寸长,麻雀叫过五六声,杨树叶儿欣欣然张开了脸的时候,石羊河就成了男孩子们的天堂。三两下吃完中午饭,碗一放,一个个悄声无息地溜出家门,站在路口的大杨树下东张西望。人来得差不多了,挤挤眼,用手朝河的方向指指,便一阵烟地溜进了河中。他们中大的刚上初中,上小学的最多,再小的被爷爷奶奶看得紧,出不来,只能哭闹一阵,让奶奶拿些零食哄一哄罢了。
正午的河水虽然有点凉,但还是挡不住压抑了一个春天的梦想。清清的河水静静地流淌,水中清晰的倒影便摇曳起来了。站在岸边,你一眼就能看见成群结对的小鱼在水中招摇。忽然,从水草中窜出几条大一点的鲫鱼,岸上马上传来一阵呼叫声,紧接着就有人脱衣解带准备下水了。捉鱼,不仅是个学问活儿,干这活儿之前,你首先得有流血的准备。石羊河中有一种蚂蝗,黑色的身子伸缩自如,伸开三四寸长,芨芨棍般粗细;收缩时成一团,象个小圆球。蚂蝗一头尖尖,另一头有一个吸盘,它用吸盘吸住你的皮肤,尖尖的那头钻进你的血管,在不痛不痒中吸着血,我们叫它“吸血鬼”。当在水中忙碌的你,感觉腿脚某个地方有点胀胀的时候,蚂蝗一半的身体已经钻进了你的血管,鼓起一截。胆小的吓得乱跳乱叫,胆大的微微一笑,拿起妈妈做的布鞋朝鼓起的那头打去。打一下,蚂蝗退一点;再打一下,再退一点。差不多了,伸手抓住蚂蝗吸盘的那头用力一揪,它就瘫在你的手掌中了,搓几下,马上变成一个圆鼓鼓的肉球了。你要看热闹,就把它放在石片上,用鞋底使劲一抽,吵闹哄笑声中你会看到血花四溅;你要解气,大伙就一齐上阵,先用尿把吸了血的蚂蝗浇个够,然后用一根木棍挑起辗转翻侧的“吸血鬼”,把它狠狠地扔到滚烫的沙滩上,看它扭曲翻转垂死挣扎,在欢笑和尖叫的混响声中忘了所有的快乐和不快乐。这些“吸血鬼”们呀,等晒干了还能把你当药材卖呢。
其次,你还得了解鱼儿的习性吧。鲫鱼胆小,鲢鱼善跑,泥鳅能钻,草鱼爱跳。抓鲫鱼,人要多。几个人在水里一起搅和,水很快就浑浊了,鲫鱼要么四处乱窜要么乖乖地藏在水草底下。这时候,一部分人用双手拢成半圆形,在水底一摸一按,十次中总有一二次收获;另一部分人则在水草中泥坑里一拢一攥,感觉有东西在挣扎,十有八九就是一条鲫鱼,其余一两次则是青蛙了。我就是一位捉鲫鱼的高手,大多数的孩子碰到四五指宽的鲫鱼容易被挣脱跑掉,我却不会。我有一个秘诀呢,那就是按住鲫鱼后一定要用大拇指抠进鱼腮里,这样再大的鱼也得乖乖地任你摆布。捉鲢鱼,可不能用手摸了。鲢鱼机灵苗条跑得快,用手是很难抓到的。我们采取的是“围剿”战术,所有的人都围在一起,留一个缺口,晃着树枝慢慢地把鱼赶进一个死水坑里,迅速用树枝泥巴堵上缺口,然后用水桶水盆往外舀水。不一会儿,水浅鱼现,你用两根手指头就能夹起一条已经筋疲力尽的鲢鱼。河中的泥鳅太小看不上眼,草鱼难看又不好吃,抓到了算是意外的收获吧。该清点战利品了,照例是抓大放小以少送多,三指以上大小的用双叉的红柳条串起来,小一点的仍进河里让它回家吧,还得挑几条机灵漂亮点的“三尾巴”装进弟弟的玻璃瓶中,送给他能高兴好几天,放羊的时候会跑得最快最勤呢!
泡在河水中的光身子们还舍不得上岸,就来比比水性吧:在水最深的“磨坝”处,能淹住你的鼻子的地方,先看谁的“狗刨式”游的快,再比谁的“猛子”扎得远,最后赛谁“憋气”时间长。玩累了,就上岸去,躺在有点烫人的沙滩上“缠身子”,柔柔的沙粒摩挲着你的肌肤,暖暖的沙滩亲吻着你的身体;闭上眼,听群鸟在合唱;深吸一口气,花香和着阳光沁入肺腑,心旷神怡。不远处,树头相牵,树影婆娑,好象母亲的手拍打着你,让人昏昏欲睡,流连忘返。
夏天过得总是很快,秋天转眼就到了。红柳早早换上了秋装,杨树叶黄了但并不落下,沙枣红了还高高地挂在枝头,河水凉了,小鱼回家了。石羊河里没有了夏天的喧闹,静静的河水缓缓地流淌,你一眼就可以看得见河底,河水冲涮着的沙粒犹如颗颗珍珠反着光,眨着眼呢。打沙枣的来喽!男孩女孩齐上阵,你用棒子打我用袋子装。打下的沙枣拿回去让妈妈蒸一蒸,洒点酒,放在缸里捂几天,酸甜中带着酒香,可好吃了,它还能夹在馍馍中当点心呢。
冬天想念石羊河了,约几个人去溜冰吧。河面没有封冻,岸边的冰太薄,不敢下去滑。有几个水坑上的冰结实,但冰面太小,不好玩。那就等到腊八打“腊八冰”吧。一家人拿洋镐铁锹打回的冰,先献几块在田间地头,然后你就可以吃了。咬一口,咬不动;舔舔吧,舔几口,冰块变亮了,仔细瞧瞧,呀,冰里面有椭圆的小麦鼓圆的黑豆扁圆的蚕豆,还有咧歪了嘴的玉米粒呢。冰小了点,干脆整个儿含在嘴里,鼓着腮帮子使劲嚼吧。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了舌头,没有了牙齿,没有了感觉。一切都在冬天里沉睡了。
我的童年没有兴趣班,没有辅导课,只有那条静静的石羊河;我的童年也没有高高的烟囱,没有成排的楼房,只有绿草绿叶流水游鱼;我的童年还没有汽车和雪糕,只有鸟鸣和冰块;我的童年更没有臭气熏人的污水,只有舀起就能喝的泉水……。童年的时光在河水中静静地流淌,一去不复返,它只能珍藏在生命的记忆中。可是,石羊河的春天总不能停留在回忆里呀,石羊河的春天会到来,童年的情景会重现。“这不仅是一个决心,而且是一定要实现的目标”,会的,一定会实现的。
第四幕:哭 泣 的 骆 驼
前几天,我给学生发《爱我石羊河》的教育读本,看见书的封面上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树林间草绿水清的石羊河,另一张是茫茫黄沙上孤独站立的一峰骆驼。
骆驼,我记忆中最早的是在那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分责任田时,生产队的十几峰骆驼被生产队长买下宰杀时的场景:大人们把拉骆驼“鼻卷”的绳子短短地栓在大树上,哄骆驼卧倒后,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死死压住骆驼的头,其他人迅速用大拇指般粗细的麻绳紧紧捆住骆驼的四蹄,接着明晃晃的刀便逼近了骆驼的喉咙……。这时,骆驼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四蹄乱蹬,头努力地向上抬,喉咙里发出“嗷嗷”的吼叫声,瞪圆的眼睛里先是愤怒,后来变成了绝望,再后来是一片模糊。这血腥的屠杀场面吓得围观的小孩子们叫哭连天,身边的老人赶紧用手紧紧捂住他们的眼睛,生怕孩子见了晚上会做恶梦。这些骆驼,过去为生产队犁过地打过场,拉过车驮过粮,如今却象猪象牛象羊一样地被曾经的主人屠宰。等现场平静下来,我们胆大一点的孩子才敢试探着靠近,走近看看正被大人们剥皮割肉的骆驼,摸摸平时不敢碰的骆驼头。如果你注意到了骆驼的眼睛,就会发现它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眼眶里含着泪水,汇聚成的一滴滴泪珠儿正顺着长长的睫毛慢慢地滑落……。原来,骆驼在哭呀!
后来,我看到的骆驼是在田间地头。那是上师范时和同班四十五位同学去民勤游玩,本想在这块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交界的绿洲上,能看到成群结伙的驼队从我们面前缓缓走过,听着悠扬悦耳的驼铃声悠长回响,回味那赶驮人深沉的歌声里飘过轻灵的鞭影。甚至还可以在现场学唱《梦驼铃》中的一段:“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但我们在民勤找了一整天,只看见了一峰骆驼,它已经脱了很多的毛,还戴着花花绿绿的肚兜,拉着一副“七寸犁”,在尘土飞扬的干沙地上顶替着两头牛的工作。骆驼的步伐沉重而有力,身后一条条沙浪上下翻滚;扶犁的农民用力地把犁铧往沙土里压,甚至整个儿身子都爬到了犁铧上,面前一垄垄黄土翻起又落下。
我们觉得有点好奇,怎么骆驼也戴上了肚兜了?犁地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结实的庄稼汉子,黑黑的脸,总是眯着双眼,笑的时候脸上便堆满了皱纹,就象晒干了水分的胡萝卜。他乘着休息的空儿告诉了我们答案:这几年干旱,雨下得少,缺水;上游石羊河的水变浅了,来到下游的水也越来越少了。人都缺水,更何况庄稼牲畜。没水,就没有庄稼牲畜;没水,也没有草场树木;没有草场树木,就挡不住沙子;挡不住沙子,就没有骆驼吃的草料。骆驼一次吃饱喝足后,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不喝,但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时间。没草吃的骆驼的征兆是褪毛脱皮,掉了毛的骆驼根本挡不住蚱蜢蚊子的叮咬,只好给骆驼穿上“衣服”抵挡一阵子。饥饿的骆驼开始时站不起来,慢慢地,腿就水肿,最后腿肿得象水桶一样,并且开始溃烂。没等烂完,骆驼就死了。更可怕的是骆驼本身有双层睫毛,可抵御风沙,但是在越来越强烈的沙尘暴面前,骆驼也没有办法抵抗。被风沙打瞎眼睛的骆驼,由于看不见草,结果只有被活活饿死。听着听着,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这样的镜头:瘦骨嶙峋,大块脱落皮毛的骆驼,站不起来,载不动农民拉水的车,被沙尘暴打瞎的双眼中含着浑浊的泪水……。
临别时,这位朴实的汉子还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小骆驼在出生半个小时后就能自己站起来。但是现在由于母骆驼的营养不良,小骆驼生下来就极度虚弱,经过几个小时的挣扎,腿软得就是站不起来。这时主人想过去帮忙也不行,因为母驼根本不让人靠近小骆驼。这样小骆驼就必死无疑了。只要小骆驼死了,母骆驼就会守在小骆驼的身旁嗷嗷哀叫,声音凄惨悲伤,听到的人无不心酸。就这样七天七夜,母骆驼不吃不喝,也会跟着死去。————这是母与子的感情,犹如石羊河和河旁人家的感情。
前几年,我看见的骆驼是在西郊公园里。那是一峰褪光了毛的瘦小的骆驼,空瘪的双峰无力地低垂着,脊背上搭着原本用来驮货的木架,上面铺着猩红色的毛毯,现在却用来驮游客上山观光。山是在公园东北角的一座小土山,山上没有一棵树,只有零星的野草。游客骑上骆驼从山的这头盘旋而上,然后骑着骆驼从山的那头盘旋而下,就这样转一圈十元钱。骑的人少,看的人多。我只敢看着骑在骆驼上的那人小心翼翼眉开眼笑的样子,却不敢注视骆驼的眼睛。我怕看见那双眼睛中含着的眼泪,更怕那一滴水落下来,干枯了,———剩下可以流的,就是人类最后的一滴眼泪了!后来,这峰骆驼也不见了,大约也一定死了吧。
最近几年,我看到的骆驼是在电视里画纸上和照片中。电视里的骆驼在那遥远的地方,画纸上的骆驼画家画不出眼睛里的泪水,照片中的骆驼缺少绿树绿草和流水做的背景。骆驼,有“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面对水缺草死,草死沙进,沙进人退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难道要像熊猫一样稀少,难道要像恐龙一样灭绝?一个了伟大而坚定的声音传来了:“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仔细想一想吧:如果民勤变成了第二个罗布泊,那么谁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如果今天哭泣的是骆驼,那么明天流泪的又是谁呢?
第五幕:想 念 青 蛙
五岁的女儿正在上幼儿园,她最爱看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了,看完一边,还嚷着要看第二边。看够了,我就问她:“小蝌蚪的妈妈是谁呀?”女儿马上回答:“大青蛙。”我接着问:“大青蛙长什么样子呀?”女儿一口气回答到:“四条腿,大眼睛,绿衣服,白肚皮,走起路来蹦蹦跳跳。”边说边学青蛙的样子一蹦一跳起来,我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青蛙,农村也有人叫它“田鸡”,在二十多年前的石羊河旁随处可见。
石羊河里的青蛙多,先要从蝌蚪多说起。六月一到,河水变暖。河里的小蝌蚪就拖着长尾巴摇头晃脑地忙碌起来了,它们好象跟下河摸鱼洗澡的孩子约好了似的,一齐在深深浅浅的河水中时隐时现。最担心的是河里发大水,一场大水过后,在一湾湾水坑中,总有挤在一起吵吵嚷嚷的黑身子大脑袋们。它们的生死只能看运气了。运气好的会碰上友好的小朋友们,那些黑脑袋也会挤在一起,用手在水坑和河水之间挖一条水沟,弯腰看比赛似的,吆喝着蝌蚪一个个游进母亲的怀抱。运气不好的,碰上拿笊篱提竹筐的大人们就惨了。这些人用笊篱捞起扭着身子挣扎的蝌蚪,把它们扣进竹筐,提回去喂鸡。据说用蝌蚪喂的鸡不生病还下蛋多——这样,蝌蚪好歹做了点贡献。最坏的是运气,那些挤满蝌蚪黑脑袋的水坑没有人发现,几天后的结局就是水干蝌蚪也干了。
等到蝌蚪变成青蛙的时候,石羊河的天地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小鸟在树枝上边跳边清脆地歌唱,啄木鸟机警地和着节拍敲着鼓点,蝴蝶穿着各色的裙子在草从间翩翩飞舞,蜻蜓轻盈地悄悄吻过水面。最活跃的是青蛙。树荫下,青蛙在低吟浅唱;草丛中,青蛙正纳凉休闲;岸边的空地上,还有青蛙在小朋友的呐喊助威声中,比赛“跳高”和“跳远”呢。有一点风吹草动了,吟唱的停住了歌声,东张张西望望;纳凉的一跃而起,嗖地一下,射入水中,吓得河中聚会的小鱼小虾没头没脑地四处逃窜。好一会儿,青蛙才从远处调皮地探出头,睁着大眼睛张望着周围的动静。如果你够机灵,也能抓得住青蛙。你可以把它放在手掌心,看它高高地跃起,又远远地落下。也有贪心的小孩抓住青蛙舍不得放手,人的体温会烫伤青蛙的皮肤,那样青蛙也许会被烫伤也许会被捏死。死了的青蛙不能让它肚皮朝天地躺在地上,只能深埋在泥土里。听老人们说,肚皮朝天的青蛙是在“告天”,行凶的人会遭到报应呢。
后来,听说把青蛙熬成汤,小孩连肉带汤吃了可以祛湿驱毒。于是青蛙首先成了小孩子的美餐。紧接着,城市里的餐桌上就有了用青蛙做的菜肴,街道两旁烧烤摊的火炉上支架起了一串串的青蛙,据说家家生意都很红火。很快地,就有人抓捕,有人收购,他们都想靠青蛙赚钱致富呢。于是,青蛙东躲西藏南逃北窜,日子就难过起来了。同时,田地里用化肥代替了农家肥,农药抢夺了青蛙的食物。当青蛙吃了喷洒过农药的害虫,就把自己也毒死了。更可怕的是,石羊河里的水迅速地变浅了变黑了变臭了,鲫鱼不见了,鲢鱼绝迹了,泥鳅的肚皮朝天了。青蛙呢?没有了水源就没有了家园,没有了家园,面临着要么搬迁要么死亡的选择,就象生活在沙漠中的人们。转眼之间,青蛙在石羊河旁就消失了,石羊河周围没有了青蛙的身影。没有了绿衣服白肚皮大眼睛的青蛙,出现了一种麻皮肤灰肚皮小眼睛的蟾蜍,跳不高也跳不远,我们叫它“麻癞呱”。据说这是青蛙的变种,可它不是青蛙,我喜欢的不是它。
看着女儿蹦蹦跳跳的样子,多象一只小青蛙呀!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人类总不会把自己的儿女也像青蛙一样吃了吧?我们总不能断了石羊河的水源,毁了自己的家园后,也像青蛙一样来一次变异吧?想一想青蛙的遭遇,你就有明确的答案。
第六幕:母亲的鱼汤
最美好的回忆莫过于纯真的童年,最美味的菜肴莫过于母亲的鱼汤。童年的时光浸泡在河水中,一去不复返;母亲做的鱼汤却能年年喝得到,让我永远无法忘记。
母亲做汤用的鱼是我从石羊河里抓来的,常常是我杀鱼﹑清洗后,把鱼交到母亲的手里。母亲总是先要分开鱼肚,仔细检查还有没有粘在鱼肚内壁的一层黑色的膜,据说那层膜有毒,人吃了会头晕呕吐甚至昏迷死亡。母亲检查满意后,再用清水冲一遍,这才把一尾尾鱼从大到小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海碗中,撒上两撮盐,浇上几滴醋,再用另一个海碗扣严,只等饭后下锅清炖。
天还没有黑,一抹晚霞映照着天边的云,我们一家六口匆匆吃过晚饭,碗筷一放,开始忙碌起来。爸爸烧火,妈妈掌勺,我们姐弟四个围着灶台向锅里张望。母亲先在热锅底里刷上一圈油,待油八九成热,她就慢慢地把鱼一条一条顺锅沿滑下去,锅里马上传来一阵哧溜声,飘出的缕缕香气,引得弟弟吸起了鼻子。当一面的鱼由白色煎成淡淡的金黄色,就翻个个儿,再煎另一面。煎好后,添三大勺自家门前“压井”中压出的带着甜味的水,盖上木制的锅盖,先用大火熬十五分钟左右,调两撮盐,再盖严锅盖捂七八分钟,一顿美味佳肴就端上了饭桌。
在这个从爷爷的爷爷哪儿传下来的沙枣木饭桌周围,母亲笑眯眯地把鱼搭配分好后端给每一个人,常常是弟弟的鱼最大最少,爸爸的鱼最小最多,其他人的都差不多。她总是自己不吃,微笑着看我们吃,不时地叮嘱:“慢点,慢点吃,还有呢,别让刺卡着。”父亲偶尔接上一句:“才不会呢,猫儿不可能让鱼刺卡住自己。”父亲说的真对,不仅我们姐弟几个,就是多年以后,我的女儿侄子侄女,个个好象天生都会吃鱼,他们从来没有被鱼刺卡住过。等我们吃完了自己碗中的鱼,母亲就把她碗里的鱼给我们一人分一条,剩下最后的一条自己才慢慢咀嚼品味。父亲则只给弟弟夹一条,趁我们不备悄悄地给母亲夹一两条过去。
最痛快的是喝鱼汤。母亲熬的鱼汤白白的浓浓的,上面还漂浮着零散的金黄的油花,有点像牛奶,但牛奶没有这样香。端起碗,沿着镶蓝边的碗沿深深地吹一口气,浅浅地喝一口还烫嘴的鱼汤,一股暖流一直热到你的肠里胃里。喝进的是热热的鱼汤,呼出的是暖暖的鱼香,那种感觉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等鱼汤凉了点,只要嘴碰到碗沿上,一口气喝不光碗中的汤,碗是不会放下的。吃饱喝足了,父亲总是要我们出去走走,要不然会“积食”呢。
后来,我参加工作挣钱了,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也吃过了不少,但它们总没有母亲熬的鱼汤那么香。我也常常从鱼店里挑几尾一斤左右的鱼自己熬汤喝,但总是熬不出母亲的鱼汤的那个味儿。我也向母亲讨教过她的秘诀,但就是熬不出那份浓浓的鱼汤,不免总有点遗憾。
直到我的女儿母亲的孙女过六岁生日的那天,我给母亲帮厨时,才发现了母亲的鱼汤的秘诀。在烟雾缭绕的厨房内,母亲弯着腰把鱼一条一条慢慢溜进锅里,锅里立刻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紧接着添三勺水,盖上木制的锅盖,大火熬十五分钟的左右,调两撮盐,再盖严锅盖捂七八分钟。母亲揭开锅盖,用勺子舀半勺汤,尝一口,轻轻地咂咂嘴,再尝一点,再使劲咂咂嘴,然后小心翼翼地调进一小撮盐,盖好锅盖,拿起烧火棍,坐锅台前,把火轻轻地拍小一些,就蹲在那儿守侯。我看着母亲的脸,才发现原来那圆润白皙的脸盘不知什么时候变得瘦削惨白,皱纹悄悄地爬满了额头和脸颊,蚕食了鲜活的青春,留下了干枯的外壳,沟沟渠渠,交错相连,没有鲜活的流水,只有一片荒凉;原来明亮的双眸远远地扔在了那遥远的记忆中,混浊的眼珠里看不见生命跳跃的影子,只有一片模糊混沌,沉闷的死水激不起一丝微谰,偶尔闪过的亮光也瞬间即逝。一缕花白的头发顺额头温柔的贴在的脸上,泥炉中的枝条在劈劈啪啪地燃烧,一片火光慈祥的照着这张已经老去了的脸,恬然,柔和,慈祥,泛着圣洁的光芒,就像一张菩萨的容颜。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鱼汤中原来多了一样调料,那就是爱。
母爱无言,母亲把自己对儿女的爱融化在浓浓的汤中,你能不感受到它的醇香吗?天下的美味佳肴又怎么能和融进了母爱的鱼汤相比呢?母亲河无言,无言的河水悄悄地滋养着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滋润着你的每一寸肌肤,浸入你的身体融进你的血液,成为你生命的支柱和生活的基础。读懂母亲,你才能读懂石羊河;关爱石羊河,你才会关爱母亲。母亲就是石羊河,石羊河就是母亲。谁愿意毁坏自己的母亲,做骂名远扬的不孝子孙?谁愿意毁灭自己的母亲河,做遗臭万年的无颜父母?没有,没有人愿意。
否则,我们面对古人,无颜;面对后人,无脸!
后记:2007年5月2日,我回老家去,看看家乡的父母,看看家乡的石羊河,发现父亲老了,母亲老了,侄子侄女长高了。十岁的侄子得意地告诉我:昨天,5月1日,我们在河里抓了九条鲫鱼呢。我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心想:石羊河的水已经变清了,河中的鱼虾正在回来的路上了吗?石羊河真的变年轻了吗?我的童年的光景重现了吗?我得赶快到河边看看去,去看看我的母亲,去看看我的母亲河!
(作者联系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黄羊镇广场中学 邮编733006 电子邮箱ywy0603@163.com)